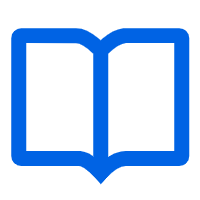几个月以后不允许堕胎?
我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被告陈有西,是他接受央视《焦点访谈》栏目采访后不久,2015年8月25日。 当时,我和同事们刚刚从医院做完手术,刚从楼上下来,就看到电视台记者正在向陈有西提问关于“药流”的问题。我正想解释一下这个案例中所谓的“药流不全”,其实是指孕囊已经排出,只是有大块组织物残余,而并非服用药物后导致胎停育,这时陈有西打断了我。 “你们医生都知道的,药流就是服药将胚胎杀死,然后孕囊脱落。”陈有西语速很快。 “这个药流不全是因为她本身出血比较多……”我又开口道。 陈有西又一次打断了我的话。 “什么叫药流不全?你的字典里怎么没有这个词儿?这词儿是你们医学术语!”他略显不悦。 看着这位颇有些名气的律师,我想起几年前《法制晚报》的一篇专访: “你经常为涉黄涉毒的人员辩护……有人说你是‘流氓律师’。” “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正义的律师,我也不希望这样。如果每一个犯罪的人都像他(指被告人)这样,认罪态度好,积极赔偿,社会危害小,我当然愿意为他辩护;如果他像李天一那样恶劣,我就是再喜欢他,我也不会去帮他。所以不能说我是在为流氓辩护。我是为罪轻的人辩护。” 陈有西确实是个好律师。
几天后的庭审过程中,当我陈述完案件事实和医嘱后,陈有西质问我: “根据你所掌握的常识,是否认为怀孕两个月时服用药物可以导致流产?” “我不确定。”我回答说。 “那你是否同意三个月后再做流产手术?” “我不同意。”我说。 “你为什么不同意?” “因为妊娠三月内任何终止妊娠的方法都有可能对母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那你说的三个月以后再流产指的是哪种方法?” “人工流产或引产。” “也就是说,三个月以内的自然流产你需要干涉吗?” “我没有说我要干涉,但是我的治疗意见被采纳之后,患者却以此为由拒绝进一步治疗并停止续费,所以我只能说非常遗憾,我只能期待下次再来。” 我顿了顿,接着说道:“作为医生,我们建议尽可能避免人工流产,而采取避孕措施。” 庭上双方争论的问题是,医院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给患者造成损害。面对对方的质疑,我几次重申医院的诊疗原则。当陈有西再次重复他的疑惑时,我有点按捺不住了。
“我认为医院已经尽到告知义务且具有相应资格,不存在过错。”我反驳道,“如果你坚持认为医院存在过错,就请出示相关证据。” 庭审结束后,我走到门口,听见陈有西和他的当事人还在不停地交谈着什么。突然,陈有西转头看向我,笑着伸出了手。 “蔡医生,我们可以谈谈吗?” 我有些意外,但立刻点了点头。 “我想听听你对药流的看法。”陈有西说。 我们来到附近一家律师事务所,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陈有西开始阐明自己的观点。 “药流不干净的原因是什么?”他问。 “这个不能说绝对,但我们发现有的孕妇对药物反应敏感,用药后胎儿立即死亡,这样的病例也有发生。”我答道。 “为什么有些人用药后胎盘自动脱落?” “这个是随机事件,可能和个体差异有关。” “有没有办法提前判断哪些孕妇适合用药物流产?” “目前没有这个技术。” 我摇了摇头。 “既然没有适应证,那医疗机构擅自给患者行药流就属于医疗事故了,对吗?” 我没有回答,但表情已经表明了我的意思——这家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并无不妥之处。